《文化周末》推出“东莞学人”系列专题,选《东莞学人文丛》中所述人物,介绍其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带领读者一同踏上寻找东莞当代学人之路,领略东莞人文社科学者的精气神。本期聚焦教育家张寿祺。

张寿祺先生的一生都在行与知中求索,在他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足迹遍及广西、海南、广东等少数民族聚集地,他对海南岛民族历史、疍家人以及“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如今依然影响着后辈学者。
张寿祺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协助梁钊韬先生重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中国人类学学科以及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忙碌的学术与教学工作中,张寿祺心系故乡,与东莞文史界联系密切,积极为故乡文史提供稿件、推介东莞历史名人,赤子之心让人动容,印证着当代东莞学人低调质直的学术品格。

80年代初张寿祺(右二)到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调查。
学海回眸
知行合一传承学术精神
张寿祺,1919年出生,广东省东莞市人,童年时在骆冕廷办的“紫衢学塾”读书,1932年考入东莞中学,中学期间曾发表过不少文艺作品。1938年考入中山大学。1943年,大学毕业后的张寿祺到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在任教期间踏遍瑶族、苗族、侗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
1948年张寿祺回到广州,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研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教授和民族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校期间完成《瑶族山居因素分析》,并刊登于《西南民族》。
1950年,张寿祺被聘为海南师范学院(海南大学前身)文史讲师,并兼学院附属中学校长。1952年7月,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教育家梁钊韬先生受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组成调查小组深入海南岛五指山地区,搜集黎苗各族的历史文物并进行历史调查研究,准备在武汉举行大规模的中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
张寿祺先生当时正在海南工作,也被委派参加此项工作,带领一队调查小组前往乐东番阳区、万冲区、保亭毛道区和三平区展开实地调査。在调查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的七十多天里,张寿祺与调查小组从海岛的西南行至东北,横贯黎区,步行几百里,每天翻山越岭,深入黎家村寨,收集到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3年,张寿祺先生被调回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任教。因参加当时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于1957年至1959重返海南岛,并在乐东县三平村发现黎族人民仍然保留的原始钻木取火技术,成为中国最早发现这一原始技术的人,证明了中国古代钻木取火的传说并非虚构。
1960年,张寿祺先生将田野考察成果汇成学术论文《海南岛黎族人民古代的取火工具》,发表在《文物》杂志第六期,并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发表论文《中国古代取火方法考证》,全面说明钻木取火技术的科学原理,追溯人类取火方法的起源。
为保证资料的严谨与真实,张寿祺先生于1984年、1985年再次前往海南岛实地考察,与曾经收集的资料反复校对,写成论文《海南岛乐东县番阳区黎族群体变化的研究》,著名生物学家、海南大学校长林英教授为之作序,并称之为“作为研究海南岛民族历史和少数民族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开端”。1986年,这部著作由海南大学出版。

1979年张寿祺先生带学生到野外考古实习。
回顾张寿祺的学术生涯,知行合一是他研究状态的最好总结。1952年,张寿祺在海南岛文昌县水上居民区体验生活,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下定决心研究这个群体。1966年,张寿祺先生被下放到“洪圣沙”“白兔沙”水上居民聚集区落户,与水上居民共同生活一年,加深了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为研究水上居民(疍家)的历史、生活和文化,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1984年至1988年,张寿祺深入珠江口“疍家汇集区”实地调查,足迹遍及番禺莲花山、虎门、新湾渔港、龙穴岛一带及珠海市斗门县各渔乡,重访三亚市水上居民聚居区,并到西江、北江进行追溯。
“人类学家必须长期深入持久地进行田野考察,必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是张寿祺先生恩师杨成志先生的学术理念,张寿祺先生用一生的行动传承着师者严谨、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经过近四十年的资料积累,张寿祺完成《疍家人》一书,并在1991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疍家人》揭开了水上居民的神秘面纱,并理清其族源之谜,为世界描绘了一幅中国南方水上居民群清晰、准确的图绘。
除了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张寿祺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协助梁钊韬先生重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并与梁钊韬先生共事于此,逐步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具有学术思想和创新精神。1986年美国传记协会主编的《世界名人录》载入了梁钊韬先生的名字,称“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系是世界上真正的人类学系”。

1984年同杨成志(左)教授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门前合照。
出书逸话
心系东莞文史 传承学人精神
东莞学人历来有整理、总结前辈著作的优良传统,这是继承东莞文脉、弘扬前辈业绩、激励后来者的最好方式。从张寿祺为东莞文史界推荐张荫麟,到如今东莞政协文史委员会为更多东莞人推荐张寿祺先生,东莞学人的传承精神永存。
上世纪80年代末,东莞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荫麟的著作不如现在这样流行,张寿祺先生开始在东莞文史界大力推介张荫麟先生。在东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后称文史委员会)1987年、1998年编撰的《东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29期中,分别刊登着张寿祺的文章《记一位早逝的天才史家张荫麟教授——〈张荫麟先生传略〉一文读后补遗》与《史学家张荫麟教授与他的〈中国史纲〉(上古篇)》。
心系故乡的张寿祺,与东莞文史一直有着联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寿祺先生多次接受东莞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马汉民先生与当时文史委员会主任杨宝霖先生的约稿,在《东莞文史资料选辑》刊登三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关于张荫麟先生学术与生平的文章。
正是这种传承精神,让东莞文史人心中一直挂念着张寿祺先生。2009年,东莞市政协决定征集出版《东莞学人文丛》,张寿祺先生的名字与李锦全、叶渭渠、胡守为、罗晃潮、李式金等人的名字被最早列入其中。
“因为张寿祺先生与东莞文史的联系一直很紧密,进入政协时就知道先生大名,但先生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退休之后移居到澳洲,所以我们也比较少见面。”东莞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炳球说,东莞文史界与张寿祺先生生前联系密切,但想为他出书时他本人却已仙逝,无法联系到他的家属为文史委员会授权。
张寿祺先生曾协助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重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科建设贡献卓越,学术又有一定建树,心系故乡与东莞文史,文史委员会希望能为这样一位尽显东莞学人品格的前辈,出版他的第一本正式文集。
为了取得与张寿祺先生家属的联系,文史委员会找到杨宝霖先生曾在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吴建新先生。据吴建新先生介绍,他曾邀请张寿祺先生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答辩导师。后来,吴建新找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颜广文,但他们都不知道张寿祺先生家属的联系方式。
将东莞文脉传承,是所有东莞文史人的事业。当年张寿祺先生为东莞文史推荐张荫麟先生时,也是百般周折,通过书信与张荫麟的学生李埏取得联系。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文史委员会终于在广东省考古所副所长邱立诚先生那里得到了线索。在邱立诚先生的帮助下,文史委员会联络到生活在澳洲的张寿祺先生的后人张卓研、张劲研。
“得知故乡要为父亲出书,张寿祺先生的后人与家属非常高兴,也十分支持,张卓研、张劲研还亲自撰写了张寿祺先生的生平传记作为本书的跋文。”李炳球介绍,与其他东莞学人一样,张寿祺先生也是一位低调质直的学者,默默无闻地为中国人类学发展作贡献。作为东莞文史的前辈与友人,这本《张寿祺集》是故乡对张寿祺先生最好的感谢与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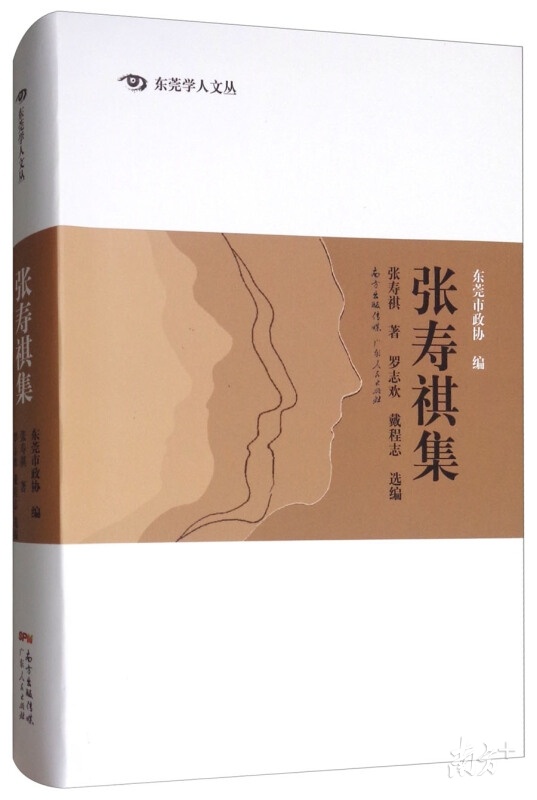
《张寿祺集》
《张寿祺集》全文近60万字,囊括张寿祺先生重要著作50余篇,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作为张寿祺先生的第一本文集,文史委员会赠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批《张寿祺集》。本书中,读者可以系统了解张寿祺先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80年代恢复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在学科理论及方法建构、田野考察实践方面所进行的开拓与创新。
学人风采
海南岛黎族人民古代的取火工具
文:张寿祺
1952年8月,我第一次入五指山黎族地区进行历史文物调査时,曾在乐东县三平附近一个村庄里找到一副钻木取火的工具,后来从三平转到番阳又找到了一些。由于过去民族学研究者和一些考古工作者的文章都未曾提到过黎族地区的这方面文物,我遂留在乐东就地进行了一些调査。1957年、1958年因工作关系,两次重来五指山区,到过琼中、白沙、东方各县,这两次虽然没找到钻木取火的工具,但一些黎族老人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黎族地区确有许多地方在使用它。
五指山区遍地野生着一种名叫山麻木的植物,它的表皮可以纺纱织布,木质可以作钻火工具。钻火的方法是,首先折下一根山麻木把它弄成扁平,在上面刻下一个浅浅的凹穴,再在凹穴的旁边刻上一条浅浅的缺槽。
弄好后,把它放在地上,再折一根山麻细枝当作小棍子。人坐在地上用两只脚把刻有穴和缺的山麻木按着,然后拿着小棍子,以一端接在凹穴上,双掌用力地把棍子搓起来,棍子急速回旋,棍子末端与凹穴接触处遂发生剧烈的摩擦。由于这样摩擦,凹穴里逐渐生出一些木屑粉末,沿着缺槽落下堆在缺的旁边。棍子末端与凹穴不断地摩擦,凹穴里遂生热,剧烈摩擦继续下去,凹穴因热而生出火花,飞出缺槽,燃着堆在缺旁的木屑粉末。见着这些木屑粉末有烟升起,就知道已着火了,把这些燃着的木屑粉末放在一把事先已准备好的干茅草里顺口一吹,茅草就燃起了火焰。
假若是两个人在一起取火,就不必用脚跺着;一个人用双手按着放在地上刻有穴和缺的山麻木块,另一个则蹲在旁边搓着棍子便可以生火了。
按人类原始的取火方法主要有“磨”“钻”“锯”“打”四种,过去黎族人民所用的这种方法,便是属于钻的类型。但黎族人民制造这种取火工具时,举凡折枝、削平、刻凹穴、刻缺槽,均使用铁刀,这显然已非纯粹原始性质的东西了。据乐东县番阳的一些黎族老人说:“最初黎族人民没有铁制工具,后来汉族人来到海南岛以后,才教会了黎族人民使用铁器。钻木取火在很古的时候本地就有了,从前没有铁刀的时候,削木刻穴是用石头工具。”在原始社会时期,黎族人民钻木取火,很可能是先将一根较粗的山麻木条折一下,再用石槌把木条打成两半,然后再用石质尖状器刻上一个浅的凹及缺,随后再折一根山麻细枝当棍子,末端接在凹里进行旋钻。
新中国成立前,黎族人民一般惯于把火种保留在灶的炭灰里,使用时才把火种拨出来,加上干草使之再燃。从过去黎族人民的这种生活习惯里,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在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年代里,每次使用这种方法取火(包括制工具及旋钻),既麻烦又要花一定的劳力,因此日常生活中有必要保留一些火种。
关于这种钻木取火的方法,在我们中国古代文献里也有一些记载。如《风俗通义》所引的《礼·含文嘉》便是这样说:“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韩非子·五蠹篇》里也说:“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这里所谓“钻燧”,我们参阅郑玄所注的《礼记·内则篇》里的“木燧钻火也”,便可以理解韩非子所谓“钻燧取火”即是钻木取火。
新中国成立前黎族人民的这种取火方法,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文献上有关这方面资料的具体内容,同时也反映出古代黎族人民在与自然斗争中也如古代的汉族人民一样掌握了这项取火技术。
至于黎族人民为什么竟把这种取火的方法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是由于过去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造成严重的贫困,不得不长期使用这种繁杂的取火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黎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大批日用品源源不绝地运到山区里去,黎族人民家家都使用起火柴,这种上古时代的取火方法遂成为历史的陈迹。
这种残留的落后取火方法,在国外一些地方仍在使用着。如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加罗林群岛、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一部分地方和非洲南部一些土人以及南北美洲一些印第安人居住区,这些地方的人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严重的压迫,造成落后贫困,以至今天仍不得不沿用这种钻木取火的方法。另外,如锡兰内部森林区里的滑达族(Veddah)和南洋群岛一些偏僻的地方也残存有这种取火的方法。
随着各地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以及经济生产的发展,这种落后的取火方法必将会成为人类历史的陈迹。
(原载《文物》1960年第6期)
学者评价
《中国专家大辞典·广东卷》中,将张寿祺先生的主要贡献概括为:“长期致力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博士研究生讲授大洋洲考古以及世界民族志、民族考古学、民俗心理学等课程。1952年第一位发现我国海南岛地区有原始的钻木取火技术的残留,并撰文论证远古时代确有‘钻木取火’。为美国官方派来的高级进修生讲授“海南岛三亚市回民与马来族系的关系”,并指导到海南岛进行现场研究。参加全国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科学史稿》等的编写工作等。
在著名人类学家黄新美的论文《珠江口水上先民(疍家)种族现状的研究》中,如此评价张寿祺先生对于疍家文化的研究:“张寿祺、黄新美从1983年底至1989年,曾以相当多的时间,深入到珠江口水上居民的汇聚区,作了实地调查研究,并到西江流域和北江上游进行追索,写出了《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考》一文,从考古遗址的考察、古文献记载、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和语言特征四个方面来论证珠江口水上居民(疍民)这个群体的来源。”
《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一文中,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陈虹利、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韦丹芳对梁钊韬、张寿祺的“民族考古学”理论如此评价:“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梁钊韬、张寿祺的《论“民族考古学”》被视为中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族考古学’的论文(梁钊韬,张寿祺,1983)。随后,学者们开始了关于民族考古学自身理论认知的探讨,一批关于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学科定位、学科归属问题、学科理论基础、学科研究方法的研究喷涌而出。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参与相关问题讨论的多为人类学学者和民族学学者,最为著名的当属梁钊韬、张寿祺与容观夐之间的论战。此番论战不但讨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萌芽时间、发展历史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而且还引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对民族考古学进行深入剖析。”
【撰文】李彤晖
受访单位供图







